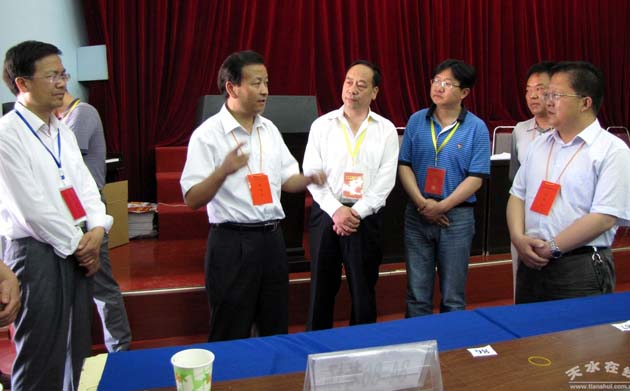| ���W(xu��)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ɽˇ�g(sh��) |
(2011-6-8 19:11:29)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W(w��ng) �� ��ӡ��� ��ӡ��� |
����1953��7�µ�һ���՚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죬�҂����e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�ڸ��C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£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У���(j��ng)�^С���ƺ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ߵĵ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ЏU�fĥ���č{�����У��K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Ҋ�r�����{(l��n)��İ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e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ҊҰ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겻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ޏ�(f��)��һ���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ߡ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ǡ��߷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ú��S��С�ò������˵�ʯ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p��Щ��s�����Ԫ��o(j��)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СС�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О锵(sh��)���ٵ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^픡��粿��̎��Ҋ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p��Ҳ�S��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B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]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Ҋ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Ɖĺ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eɽʯ�ߵ�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Ȼ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N�ꂥ�����ڮ��mҲ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d춶ػ�Ī�߿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eɽ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Ԫ��ص��L(f��ng)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Ͷ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О��Ї����Ĵ�ʯ�ߡ�߀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Č��գ��]���Ĵ����㌚�ʯ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ǘӝ������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̷���(w��)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Ե��P(gu��n)�S�ĽY(ji��)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f�Ǻ������ֺ܇�(y��n)֔(j��n)?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Ȳ��@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^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ך�̫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ԽY(ji��)�ϵ����N��Ȼ����Ǣ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нo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Ҳ���y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DŽ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ԵĘ�(g��u)˼?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ɹ�����춁K�������ڽ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ۺ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S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s�ԣ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ֻ��ijһ�N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ˌ����˵ľ��⣬�t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m����ıƽ��K����춿ɐu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Dz��y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ʷ�oǰ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ƽ٣�̎�ƫƧ֮�ص����eɽ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Ȼ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o���eɽʯ�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͵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ʯ�ߡ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߶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�Ї��Ļ��Ǻ��б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195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־�ӡ�ˡ����eɽʯ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鮋�Ԍ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Ĺ������˟���Ŀ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D�͜y�L�D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˽����eɽ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H�Ѕ����r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қ]�ЙC����ȥ���e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Y߀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eɽ�}�u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Գ����g�ӵؽ��|�����eɽ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1953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M�MС�ĵ�12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ǂ�1�ׁ��ߵ�Ů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Ұ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ǰ�ˌ����Ăܳ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ɽʯ�ߵ���Ⱥ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г��^���eɽ�@��Ůͯ���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54��2��̖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һ��11��7�Ռ��ɵġ����eɽ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ƪ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Ҍ��@�����ܵĸ��ܣ����҂��ƺ���ʲ�N�ط�Ҋ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ʲ�N�ط�Ҋ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Ȼ�X���@Щ����ʹ�Ҹе��H�С������ڽ̵�ˇ�g(sh��)�г��F(xi��n)�@�N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ƪ�����Y�f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ݻ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^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y�ÿ����@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_�е��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қ]�пɿ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һǧ�װ���ǰ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@�N�@�˵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˃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ǻ�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ͯŮ�o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Ȼ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g��u)˼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123�߃�(n��i)��ͯŮվ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ӭIJ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ĵ��Ӱ��y��ӭ�~���Ҳ�S���@�ɂ�����c��̛]��ֱ���P(gu��n)�S��ͯ�С�ͯŮ������ڿ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Թ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s�@ʾ�ˌ��ڽ̵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ص�Ц�����ڶ��o����B(t��i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ܷ���Ĺ�ͬ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ͯ��ͯŮ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ڷ�̵����Y�y��Ҋ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̏ģ���ֻ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˵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е��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C�еĻ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�@���^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ӡ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@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ˁK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ڶ��ǿ��ܴ��ڵ��˂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s�ֿ���ʹ�҂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Ϥ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춌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ܴ��ڶ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@�ɂ��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ڽ̷���(w��)�ı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(xi��n)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Č����y(t��ng)һ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@�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Ԍ�춱����ԁד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ĵ�λ����ҟo���Д��@λ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ͽ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۵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ͯ��ͯ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҃��r�ďR�Y��Ҋ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ˌӵتz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Ǹ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е��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N���˿ֵ֑�ӡ��Ҳ���ٶȳ��F(xi��n)�ڐ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ɷN���ܶ��Ǟ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(d��o)��ǰ���^֮����և������ߑ�(y��ng)���Ќ��H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ˇ�g(sh��)Ʒ���^�p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^�ǷN���ϵ�ɽ������偿և��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^�p�����eɽ��123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ڴˣ��Ҳ���؏�(f��)1953�ꌦ���eɽˇ�g(sh��)�Ľ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⌦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Ʒ��һ�l(f��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fֻ�е�123�ߵ�ͯ��ͯŮ����ֵ���^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x�߶����ܵõ��Լ��Ī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ä���Ծ�δ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��f����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ڂ����ڽ̵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Ӄ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Ǿ��кܸߌ����r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@ƪ���ĵ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x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.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ƪС�f��һ�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u���ϵ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Y����˾�̖�O��ײ���˸��ӵı�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T�W���ڏ���Ʊ�Ͻoδ���ތ��ˎ��E�e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ڡ�ֻ����ƿ�Yϣ�����ܱ��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Dz�Ʊ�����ż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춠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ŵ��˂����ُ�I�@��ֻ�аٷ�֮һ�ęC���дIJ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ʕr���ܿ���׃��һ�����IJ�ֵ�ďU�������춠��_(d��)�ĸ���ĽǶȿ������s�Ǔ������Ãrֵ�ğo�r֮�������ܽ^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R�K���E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ʹ���뵽���e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@Ȼ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ݵ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҂��ṩ���m��(y��ng)�҂��dȤ�Č����rֵ������@Ȼ����κο��w�����Բ�ͬ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dž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^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ʯ�ߡ���ˮ���e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e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85��12��춱����|��
|
|
|
| �� �P(gu��n) �� |
|
| �� �� �] |
|
| �� �� �D Ƭ |
|
|
| |
 |
|
| |
|
|
|
|
|

 ��ӡ���
��ӡ��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