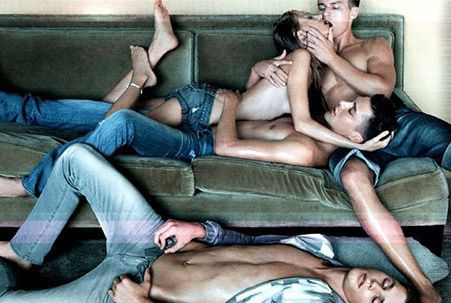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ɕ���ؕ�I��̽
��־�꣨��ˮ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C ��ˮ 741000��
����ժҪ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ϲ��h(hu��n)�Y��͛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ӡ��h(hu��n)�Y�Ǒ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R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h(hu��n)�Y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һ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֮�����ܳ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Pϵ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ӵ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Ƀ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ϡ��w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ڳ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У��䮔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ࡶ���ӡ��İ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Pϵ��
�����P�I�~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ؕ�I
�����ЈD���̖��B223�������1�� �īI���R�a��A ���¾�̖��1671-1351��2011��01-0072-05
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ϲ��h(hu��n)�Y��͛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`�����[1]�h(hu��n)�Y�Ǒ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R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2] 1530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ᄡ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ģ����ɣ���̖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C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Y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һ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ؕr�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λ�Ǻܸߵ�������ص伮��ӛ�d�P�����С��f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漰��ϲ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r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֮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P���Ӟ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c����ͬ�顰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[3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Е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ڵ��ҵ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ĕr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ӡ���ϲ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r�^���挍�ɿ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Ʒ�º͌����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ؕ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(li��n)�χ��̿����M���y(t��ng)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ʥ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ǡ����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ѽ�300�N�����漰��ʮ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֮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ؕ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ͯ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S��ɽ�ȳ��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[1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5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Pϵ�Լ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һ���γɵ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̽ӑ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ꖵ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Pϵ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ָ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x�ģ��`�Ԟ�����ǚvʷ��һ�N�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ݚvʷ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ˮ�ԡ���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䌍ָ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ꖞ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ꖞ�����Ǟ�o���@λ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ˮ�@�K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ܲ��ɷֵ��Pϵ����(j��)�P���{��Ͳ�����P�Y�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u���Pɽ�����f�^ɢ�P��μˮ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ˮ��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(j��ng)ע��μˮ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μˮ���֖|��(j��ng)��ߞ���ϡ���μˮ�֖|�����ꖹ�ˮ���ɡ�ˮ�����Rɽ֮��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ˮ�|��ɢ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ӏ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ˮ�֖|�^ꐂ}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(j��ng)��ꖹ����]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κ�B��Ԫ����ˮ��(j��ng)ע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g߀ʢ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ꖵ�̎μ�Ӄɰ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u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vʷ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Ӂ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ĵ�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ǎ��I��?sh��)�����菡����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���ӛ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sh��)ذ���߀�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P���z���У����e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в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´壨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_����̻��ϡ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R�����Ͼ�ɽ������ӟ������z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^�ӣ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ɽ�����ɢ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ꖹ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ꖳ���֮��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w��̎�����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¡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Դ��ʠ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ɽ��̩ɽ�R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ú����صص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ʢ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̴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߀�е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ˣ�ȫ���ʿ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ϣ����R��Ԫ����̎�Cͽ����־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[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̅f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L�η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Ļ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ǵ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̾��^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߅�^(q��)��˶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P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g�ڂ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o�P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ĽǶ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ڸ��C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طֲ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h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܇����R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䬺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Ŀڂ�ʷ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]�ϵ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̻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ƽ���[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ľ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Ӟ醢�σ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a����Ҳ�С��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g�ڂ�ʷ�����@Щ�Α��c����һ؞�����ġ��в���֮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ƴ���ˇ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͡��Ƈ�ʷ�a���ȕ�����Ƶ�ӛ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]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ڂ����]�б����ؕr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ʷ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һ���f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ĵ�Ī֪���K��һ�P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հ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ϻ�Ӳ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ġ��ӌ��[�ӡ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]�ϲ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ӡ�һ������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δ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r��Ŀڂ�ʷ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߲���ҕ����Ҋ���b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Ļ��c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ۙ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ֻͣ����ʷ���īI�c���ҵ伮�ķ��z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Ҫվ�ڮ��r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^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չ��˵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e�`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ľ͡��Խ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���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ó��ĽYՓ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ӛ�d���Ի���Ěvʷ�¼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Ҫע�صط�ʷ�о��ijɹ�����ȡ�Կڂ�ʷ�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՚vʷ�z�棬�����ط�ʷ־�īI�����M�о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Ե��о����ŕ��ó��^����ό��H�Ěvʷ�Y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R�w����ʷӛ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DZ��L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g�r��Ŀڂ�ʷ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 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ŗ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˞���I���ľ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559��ǰ545�꣩�r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ڂ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ϲ�Ěvʷ�z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ͨ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`��־���͡���ˮ�h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ٌ������ص伮���f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n���ӡ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桶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K��ɽ�f��(j��ng)�_�v�����ɱ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ڽ���ˮ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e�^(q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c��ˮ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ĸ���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�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ٕr���[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Ě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r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z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ؕ�I�ܚ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骚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Ŷ�Ҋδ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R��Õr�˷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ñ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˥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h�x��͢����زٌW�g�о��f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ӷŗ����ڳ�͢�еĴ��֮����ί��麯���P��ஔ��߅�zվվ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Ό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Pʷ��ӛ�d����ˮ�ڂ�ʷ�C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ʡ�Ҫ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һ�ӱ��֡���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Ǫ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tҲ����֮��Ф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ʥ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�N��ƽ�w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ܺõ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܉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ӡ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ϲ�ں����P�P�һ�f��ɢ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Ǟ��˽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ǰ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{���ź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?sh��)�һЩ�ط�ʷ�о��ߡ����Ӟ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ܳ����ز���֮ʷ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{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R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ӵ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R��Ҋ�ⱻ�˂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ز���֮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Ҳ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����ϲ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㌎�f�Ǿ���Ĺ�ͬ��˼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һ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ϲ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Y�ݞ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һ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c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˵��Pϵ�����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ĵ��v�o��ϲ[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e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´ɽ���w����̎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zַ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_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顰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Ī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˷��أ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6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Ҏ(gu��)�ɣ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ı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@Щ˼��õ���ϲ���Jͬ��ٝ�p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ӵ�˼�뱻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˽��ܲ���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ĄәC��ԭί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Ǻ���˂����f�ġ��ӌ��[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
3�,��ǰ�ڵ�
01�
010203

 ��ӡ���
��ӡ���